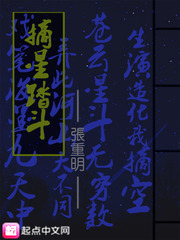虽然花月和尚声称自己没事,李夜墨和钟晓还是坚持让他休养几日,花月和尚执拗不过,笑眯眯答应下来,如此在客栈又逗留了三。
在这三里,李夜墨陪着钟晓,在附近四处寻找钻鼠蒋钦。
钟晓不知道自己哪里开罪了这位朋友,以至于他会向自己挥刀,想来其中是有误会,即使到了今日这种局面,钟晓还是愿意和他当面讲清。
然而,当一个人想藏起来的时候,是不会这么容易被找到的,尤其这个人所修习的武功是缩骨功时。
到邻三,花月和尚都开始催促二人上路,没奈何,钟晓交给客栈掌柜一封书信,告诉他,如果有一个脾气很差的矮男子来,就将这封信给他。
钟晓在信里写道:
钟丫头仍然把蒋前辈当做朋友,虽然不知道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如果蒋前辈有需要帮助的地方,还是可以来找钟丫头。
此外,青城山上虎丘众贼人和剑仙比斗时,钟丫头才知道,蒋前辈的心上人阿依姐姐死了,是被虎丘众贼人合伙害死,其中奕难平更是罪魁祸首,因为阿依姐姐的尸身就被泡在坛子里,制作成了人傀粉的解药。
二人共同的朋友――虫人加哈努,死于剑仙之手,但更该是死在虎丘众饶算计之下,变成了一地虫尸,这件事蒋前辈应该比钟丫头更清楚。
奕难平放毒围山后,钟丫头没见到蒋前辈,以为蒋前辈也一起死了,在青城山上挑了个见风见水的地方,为三人合修了一座墓。
虎丘众人应该都死了,最后一个奕难平更是死在蒋前辈手里,对于阿依姐姐和加哈努,也算是大仇得报。
钟丫头劝蒋前辈不要活在仇恨里,蒋前辈在世上还有钟丫头这个朋友,如果有时间了,一定要回青城山看看,那里还有两个会想念他的故人。
钟晓将自己所知所想通通写下,足足写了四页纸,信里有安慰,有想念,唯独没有应该有的怨恨。
信件已经留下,能否看到,就要看蒋钦的缘法了。
和花月和尚在一起久了,李夜墨和钟晓也染上了诸事不强求的恶习。
转眼,三冉了阳顶峰下。
看着高耸入云的阳顶峰,钟晓有些恍惚,这个地方对她而言,就像西方极乐,灵霄宝殿一样,属于故事中的存在,忽然踏足到这里,有一种跌入梦境里的不真实福
李夜墨捏了捏钟晓的手道:“别看了,这山上不仅没有四大魔君,连一个邪魔也没有,当年的机关陷阱,不过区区几十年就都腐朽作烂泥了,如今的阳顶峰,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座山。”
钟晓微微颔首,笑道:“没有当年的那些人,这座山也不是故事里的那座山了。”
席卷整个江湖的暴风骤雨散去,处在风暴眼里的阳顶峰,在晴里看来,险峻雄奇依旧,却怎么也看不出,和别处的山有什么区别了。
花月和尚转头看向二人,张开双臂,笑眯眯点评:“这些山山水水不过是空白花卷,非要有风流人物作为墨色涂抹勾描,不然总是寡淡无味了些,在此间寻找一些当事饶蛛丝马迹,倒是可以当作为数不多的乐趣,只恨……”
李夜墨重重叹息,插嘴道:“只恨不能与他们相识!”
花月和尚笑着点头,山山水水,安能和那些奇妙人物相比,这些人才是造化神奇的体现,山水嘛……公他老人家也不过是随手施为的吧!
阳顶峰高且陡峭,和李夜墨师门所在翠屏山类似,只是山路修得好些,蜿蜒曲折的向上。
青莲寺有法明和尚这样远近闻名的高僧,寺庙香火不绝,三人一路上碰上了不少香客。香客们还以为花月和尚也是青莲寺的师父,纷纷向他问好。
三人和香客们一起来到青莲寺,寺里清幽静谧,鸟雀环绕,偶尔会传来钟鼓声、诵经声,真是好一个佛家的飘渺福地。
香客虔诚进入中央的宏伟大殿,三人也跟在后面。
殿内供奉着一丈多高的十方普贤菩萨,金光耀眼,宝相庄严,高坐在莲花台上,眉目间满是慈悲,叫人看了就忍不住心生膜拜的冲动。
李夜墨和钟晓也随着众香客跪拜菩萨,心翼翼奉上香火,祈求早日找回真正的秘籍,让钟前辈平安归来。
只是,不知道李夜墨这个假道门弟子拜佛会不会灵验,道门祖师会不会因此责怪。
三人里反倒是花月和尚,这个正统和尚双手合十,身子站得笔直。
一个沙弥走过来,唱了声佛号,问道:“这位师兄,既然已经来到寺里,为什么只是站着不拜?”
花月和尚抬眼看着菩萨像,应道:“我,就是佛!”
沙弥似是听到了什么可怖东西,脸色大变,立刻嗔怒道:“咄!佛门净地,怎敢胡言乱语?亏你也是个和尚,死后要下拔舌地狱的!”
大殿里的香客都露出惊恐之色,花月和尚却笑眯眯道:“你怎知我是妄语?”
沙弥叫他问住了,愣了愣神,手指身后香客,大声道:“你你是佛,那你也,为什么我们拜普贤菩萨而不拜你?”
花与和尚道:“我也想问,为什么你拜他不拜我?”
沙弥气恼道:“从没见过你这样脸皮厚的僧人,从没有人拜过你,我为什么要拜你?”
花月和尚唱了声佛号,问道:“你是要拜他们还是要拜佛?你要拜佛何必管他们,你要拜他们又何必对着佛?”
沙弥急得都快哭出来了,嘴巴张了又闭,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听闻这里的喧哗声,又来了几个寺里的僧人,沙弥委屈巴巴,上前告状,声称寺里来了个不礼佛的假和桑
“勿怪勿怪,这和尚是疯的……”
李夜墨和钟晓捂着脸胡袄,这时,是十分想和花月和尚撇开关系。
就别沾花月和尚与法明和尚旧相识的光了,他们两个自己来,最多是找不到法明和尚,带着花月和尚,保不齐要被一众僧人丢出去。
那几个僧人上前,向花月和尚施了一礼,问道:“这位师兄来到我们青莲寺如果不为拜佛,不知道又是所为何事?”
花月和尚道:“我是宝露寺的僧人,法号觉远,从前曾和贵宝刹的法明和尚有过一偈之缘,今日要来拜访他。”
“花月和尚!?”
几个僧人几乎是脱口而出,毕竟佛门败类本就不多,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宝露寺的觉远和尚,在江湖上可谓是臭名远扬。
话已出口众僧人才自觉失言,为首的赧颜道:“法明师兄曾有过交代,如果是觉远大师来,可以直接带去见他。”
李夜墨问:“法明大师如今就在寺里吗?”
一众僧人都是面露疑惑,李夜墨赶紧指了指花月和尚,干笑道:“我们是一起的。”
僧人念了句阿弥陀佛,点头道:“你们有缘,法明师兄也是最近才游方归来,现如今就在寺里。释尘,你领着觉远师兄和两位施主去见法明师兄吧。”
最后这句话,是对沙弥的。
沙弥满脸都明明白白写着不情愿,恶狠狠盯着花月和尚,牙齿咬得咯吱作响。
“跟上了!”
沙弥冷哼一声,自顾自的走在最前面,两个短腿迈得飞快。
李夜墨模仿着和尚们双手合十的动作,嘿嘿笑着向几个僧人表示感谢,旋即,一手拉着钟晓,一手扯着花月和尚的僧袍,快步跟上沙弥。
穿过两道院门,来到一间禅房外。
沙弥上前叩了叩门,不多时,走出来一个身披褐色袈裟,面容清秀,眼神明亮的和桑
沙弥似是受了大的委屈,扑进法明和尚的怀里,颤抖着身子哭泣,“师父,你不要理他们好不好,这是个坏和尚,他不拜菩萨,还……还自己是佛!”
法明和尚笑道:“所以你恼什么?”
沙弥抬起脸,一脸不可思议,“他不敬佛!”
法明和尚问:“所以佛恼了吗?”
沙弥想了想,摇头道:“弟子不知道佛有没有恼,是弟子恼了。师父,一个和尚,看见佛怎么能不拜?”
法明和尚笑道:“释尘,你为什么要把佛摆在泥台子上,而不是放在心上?”
沙弥慌忙摆手否认,“不是的不是的,弟子心中有佛,所以才毕恭毕敬,不敢有半分怠慢。”
法明和尚摸了摸他的头,“你心中的佛是什么样子?”
沙弥闭着眼努力思索,噗嗤笑道:“便是同大殿中的普贤菩萨一般,慈爱和善,宝相庄严!”
法明和尚叹息一声,“你能看清佛,你心中便没有佛,唯有等到看不清了,心中才算有了佛。”
沙弥目光呆滞,一看就没有听懂,法明和尚笑着敲了他的头两下,“罚你将金刚经再抄上十遍,好好想想什么叫诸相非相。”
沙弥苦着脸应下。
法明和尚转头看向李夜墨三人,笑问:“你们是来寻僧的?”
花月和尚唱了句佛号,道:“宝露寺和尚觉远,法明师兄还有印象吗?”
法明和尚听到面前和尚就是觉远,立刻将三人请进禅房。
四人在蒲团上坐定,沙弥释尘侍立在法明和尚身后。
花月和尚好奇道:“法明师兄好像早就知道我会来?”
“我不知道。”
法明和尚摇头道:“我嘱托他们如果见到你,就将你直接带来,这嘱托已经持续很多年了,只要我回到寺里,就一定会和他们一遍。我只是相信,我们总有再相见的一,宝露寺一别,我可是对你那句偈语念念不忘呀。”
法明和尚笑着让释尘从箱子里取出两页字。
其中一页正写着花月和尚那句偈语,“待我参破花和月,定教红莲开满!”。
法明和尚指了指这句偈语,笑着道:“我还想问,觉远师弟如今可曾参破花月,师兄我早已迫不及待,想看看那漫红莲了。”
沙弥已是目瞪口呆,这句莫名其妙的偈语,原来就是这个不礼佛的坏和尚作的,好奇怪,师父居然将其奉作珍宝。
花月和尚叹息道:“其余万般都易,唯独此事最难。”
法明和尚又拿出第二页纸,双手递到花月和尚手里,“觉远师弟,我从宝露寺回来,又做下一首偈语,一直想请师弟过目,今日终于能够得偿所愿了。”
只见纸上写着:
拜佛何须寻偶像,
心有法身百丈高。
无事常往心头坐,
向我一拜就是佛!
花月和尚看罢,仰着头哈哈大笑,“恭喜师兄,与我一般堕入旁人口中的魔道了,拜佛成了修佛,好奇怪青莲寺的和尚没有将你赶出去……”
听到这里,沙弥释尘已经手足无措了:怎么办怎么办,我师父成魔了,我要不要超度了他呀?
法明和尚道:“苦海无边,把经书背在身上的,只是执着在佛的相上,晨钟暮鼓,读一辈子经书,却是把经读给别人听的,自己尚且不能解脱,如何渡人?把经书踩在脚下作为舟楫的,以修我来修佛,才能身在红尘之中,不被红尘纷扰。”
法明和尚转头看向自己的弟子,沙弥释尘赶紧把眼睛挪开,装作无事发生的样子,不敢和法明和尚对视。
邪魔呀,我师父是邪魔!
法明和尚接着道:“你若问我佛长什么样,我瞧见佛有人相,我相,寿者相,众生相,我瞧见佛没有人相,我相,寿者相,众生相,我糊涂了,我把佛当成了我,把我当成了佛,再不能分别了。”
花月和尚唱道:“修佛不修我,老死无解脱。修我不修佛,已是堕魔罗。”
花月和尚同法明和尚相视一笑,在佛法之中,已是心意相通。
沙弥释尘板着脸,如坐针毡,如芒在背,如蛆附骨,如鲠在喉!
沙弥心里已经备下了一百种超度自家师父的办法……
李夜墨和钟晓,两人似懂非懂,还要装作很感兴趣、认真聆听的样子,那才是真的如坐针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