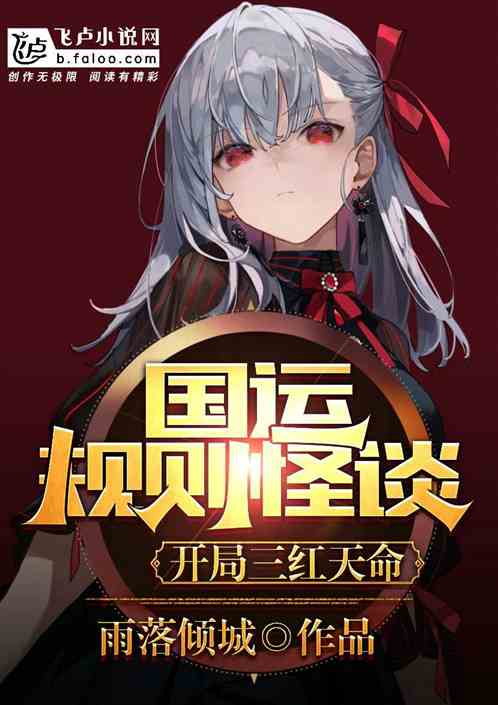夏锄生产正式拉开了序幕。
这是秋作物收成好坏很关键的一环。农工们历来把夏锄看成一年中的苦累关。
钟指导员向连队班子成员传达完场部夏锄工作会议精神后,又在连队誓师动员大会上进行了传达。王大愣作了关于“苦战四十天,闯过夏锄关,以实际行动迎接场职代会胜利召开”的动员报告。在张晓红誓师发言的鼓动下,各排都提出了一些响亮的口号,如“早晨出工三点半,晚上收工看不见,地里四顿饭!”“宁掉一斤肉,不荒一垄田!”有的还针对流感正在连队蔓延提出了“小病不下火线,重病坚持干!”连队从畜牧、工副业生产、后勤、机务、机关等各条战线压缩了百分之七十的人力上了夏锄第一线。除此,还雇用了家属临时工,要求小学校停课十天,照王大愣的话说就是:“拧成一股绳,齐下火龙关!”而第一步就是要苦战三天,攻下七号地燕麦荒!
青白的曙光和淡淡的晨雾交融,融和在黎明那淡青色月光里,露珠还在草叶上安睡,知青们开赴夏锄前线的脚步就敲响了宁静的大地。
七号大豆地的边沿上沸沸扬扬,热气腾腾,按照王大愣的指挥,以排和被压缩人员新组成的集体为单位,从一排开始每人一条垄,依次向下排成了一条长长的人线,有组织、有要求地一起向前推进。每个排所分担的地段头上,都插着迎风飘展的红绸旗和像面板般大小的毛主席语录牌、毛主席像牌。在长长的人线中间,田间游动广播站正播送着“学习大寨呀赶大寨……”的嘹亮歌声,接着,便开始播送征集夏锄战场好人好事广播稿的通知。
王大愣授予各排排长不拿垄的权力,拎着锄头跟在大伙儿后面检查质量,接接落后的知青,让不合格的返工。排长们每人手里都拎着一个使用电池的小扩音喇叭。广阔天地里,此起彼伏地响着他们的呼喊,这边喊谁谁谁伤苗重了,那边喊谁谁谁垄眼没抠干净了,那边又喊谁谁谁锄板入土浅了……二十多个扩音喇叭纵横交错的声音,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监督网,不仅纠正着铲地中出纰漏的,也告诫着别人既要保证质量,又要保证速度。
王明明的大解放专门给七号地送水送饭。他用车上的大铁桶从水房不断拉来开水,放进地头的几口大缸里。每个排都有一名送水员,用水瓢从缸里舀进水桶,挑在肩上跟在自己排的后面,像叫卖一样喊:“谁喝水啰?喝凉开水啰……”倘若有人直起腰停铲摆手,他就会麻利地挑着桶过去,摘下挂在扁担钩上的水杯舀一碗端过去。
知青们从练兵到参加这正式拉开夏锄序幕的战斗,已有所领略,原来这手工式的农田作业就这么简单,只要虚心好学,肯卖力气,不怕苦累,很快就能掌握它的技巧。
人们挥动着锄头,已形成向前推进的曲形人线后面,出现了一片垄沟、垄台、垄苗分明的田野。在这沸腾的场面里,到处都是紧张的、汗涔涔的劳动者。
火炎炎的太阳升上了天空,热辣辣地炙烤着大地,窒闷的空气越来越浓,深邃湛蓝的天空,只有几朵白云像被粘贴在天空一样,一动也不动。
随着长长的人线不断向前移动的大广播喇叭传出了音质优美的响亮声音:“同志们,夏锄大会战战地广播站,现在播送小通讯,题目是:《带病不下火线》……”
马广地挑着两半桶开水,紧跟在十六排后面正呼喊着谁喝水,一听题目立刻挑着挑儿站住了。今天早晨起来,他有点感冒,鼻子不透气,还时而滴眼泪,本想泡两天蘑菇,让郑风华一做工作,思想通了,带病跟着大伙儿来到地里,主动要求给大家送水,郑风华答应了。他立棱起耳朵琢磨:是不是排长安排谁写了广播稿,表扬我马广地呢?
播音员播送完题目以后,播送正文的声音抑扬顿挫起来:“连队机关‘一打三反办公室’白玉兰同志,身患重感冒,呕吐、咳嗽、高烧三十九度多,仍坚持不下火线,抱垄担任务,铲的速度快,质量好……”
马广地一听表扬的是白玉兰,立刻放下扁担,两颗骨碌碌的眼珠子立刻像被吸铁石吸住一样,直勾勾瞧着机关干部那片地段不动了:对,紧靠防护林带边上,那个穿着粉红色的确凉布衫,铲在机关队伍上游位置,拉锄、送锄、剔垄眼草、倒步的姿势就像跳舞一样美的那个,就是白玉兰!
他瞧着瞧着,像被勾魂摄魄似的不着边际地遐想起来。
这时,王明明开着大解放拉来两大桶水,正往护林带地头那口大缸里放水,播音员响亮的声音也清晰地送进了他的耳鼓。桶里的水都放完了,他还像鬼使神差似的紧盯着白玉兰的背影,直到肖副连长走过来吼了一声,让他抓紧回去拉第二顿饭,他才算被震清醒,瞪了肖副连长一眼,往车厢里骨碌了一下空桶,关上厢板钻进驾驶室,拽上车门,开着车回连队了。
火炎炎的太阳缓慢地爬向高空,像一个炫人眼目的火球灼烤着田野。
铲地开始不久,人们还能时时听到王大愣的声音,过了一阵子他就销声匿迹了,不知披着凉衫、倒背着手转悠到哪里去了。连队的干部,除钟指导员和机关干部一起抱垄铲地外,肖副连长在全面地指挥着。
渐渐的,长长的人线由曲曲弯弯变得散乱了,排与排、人与人之间都拉开了距离,有的图赶进度忽视质量被排长喊回返工,有的被排长当做典型召开质量分析会,影响了集体的进度。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越快的越快,越慢的越慢,休息的哨声响了,有的还在哈着腰,时而擦着汗,拼命地赶进度。
白玉兰听到休息的哨声,用锄头在垄沟里掘个小坑埋立住锄头,走到防护林边花花拉拉的树荫底下,从腰里抽出一块小塑料布铺在地上,刚想躺下,她曾所在排的十多名女知青从这里走过,几个人一起约她:“白玉兰,走,上一号去。”
这一号,是女知青们共同秘密行动的暗号,就是上厕所的意思。这茫茫田野哪来的厕所呢?夏锄练兵的那几天,女知青们为这个事苦恼过。在这炎热的夏天,即使渴得嗓子要冒烟了,也不敢多喝水,因为喝多了就要小便,护林带的小杨树林根本遮不住人影。除此之外,在一望无际的田野里谁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清楚楚,何况人线散乱以后人们拉开了距离就地休息,偌大个面积到处是人,到处是明亮的眼睛。那些男知青多数不在乎,渴了就喝,憋得慌就尿,只要稍觉人少或没多少人注意,就很快把事办完了,女知青们就不行了,难为情得厉害,总是躲躲闪闪,觉得这儿不行,那儿也不行,跑太远了吧,本来休息时间就短,又累,不等赶回来哨声就响了,那就连一点坐着休息的时间都没有了。练兵那几天,有好几名女知青,哨一响累得想休息,但又想撒尿,索性休息一会儿,不知不觉哨声响了,让尿憋得直掉泪,还有两名憋出了病。肖副连长听说以后,给她们出了个主意,哨响休息的时候,想小解的十多名知青凑在一起,不用走出多远,就地围成一个圆圈,一个接一个地替换着在里面小便。他还起个名堂,把这女知青围成的圆形厕所,叫做一号。他还要求男知青也文明点,不要在众人眼皮底下小便,用多人围成三角形,叫做二号。有些知青,特别是女知青使用这一方法后围着肖副连长拍手叫好,称赞他“真有道道”!他一挺胸脯哈哈一笑说:“这算什么道道?小菜一碟!在朝鲜打美国鬼子的时候,出的道道多了,愿意听,有空的时候好好给你们唠唠!”
有些知青听过他讲的朝鲜的风土人情,也听过他一些出道眼打鬼子的故事。有的听后哈哈笑着搂着他的脖子,有的拽着他的胳膊,称他是连队里的“老智星”。
那十几名女知青就是在肖副连长指导下一边铲地一边说了阵子笑话后走过来约白玉兰去一号的。
白玉兰感冒发烧,刚才用力铲地又出了些汗,便感不强,本想躺下休息一会儿,伙伴们一约也就跟着走了。
王明明开着大解放来到知青大食堂门前,连鸣三声喇叭后,发现炊事员抬出来的馒头黑不说,而且像是用根本没发的死面蒸的,一个个瘪瘪瞎瞎。自己肚子虽有点饿,看着这些馒头不仅刺激不起食欲,反而更加厌食了。他一下子想起广播里说的白玉兰带病坚持参加夏锄的事,忙跳下车回到家里,让妈妈急急火火地烙了两张油饼,又煮了两个咸鸭蛋,用手绢包好带上,一上车就加大油门,一溜烟来到七号地。他正琢磨着怎么把油饼送给白玉兰时,发现白玉兰被十几个伙伴招呼走了。他灵机一动,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到白玉兰要躺下休息的地方,把包油饼和咸鸭蛋的手绢往铺在地上的塑料布上一放,便悄悄地走了。
“喂——”马广地看得清清楚楚,捅一捅坐在扁担上喝开水的李晋,指指王明明说:“你瞧,那小子鬼头鬼脑地不知扔到白玉兰那儿件什么东西?”
李晋把杯里喝剩的水底子一扬倒出去,莫名其妙地问:“你没看清?”
“没有。”马广地瞧着王明明摇摇头,“好像一团鼓鼓溜溜的什么东西!”
李晋听马广地讲过潘小彪和丁悦纯调虎离山的故事,于是起了疑心:“这小子没多少好下水,可能要搞什么花名堂,喂——你去看看!”
马广地受到李晋的怂恿,格外来了精神头。他瞧瞧王明明打着唿哨,洋洋得意地走开,又瞧瞧防护林带那边稍远处白玉兰那伙女知青搭成的一号还没有拆散,便大步流星地一步横跨过两条垄走了过去。嘿,是个手绢包,鼓鼓溜溜不知包的什么玩意儿。他刚要哈腰捡起来看个究竟,忽然发现王明明有点贼眉鼠眼地正往他这边撒眸,便若无其事地忽而仰脸朝天,忽而摇头晃脑瞧着地垄沟,像用脚尖踢足球带球似的踢着手绢包回到了李晋身边。
王明明瞪大眼睛细细一瞧,在白玉兰休息处转悠的,正是马广地!上次在去空军农场的路口上和他好顿厮打,自己还用尿尿了他给白玉兰买的衬衣,心想,真是冤家路窄,自己往那里放手绢包时是让他看见了,说不定这家伙又在搞什么名堂。他心里产生了疑忌,瞪大了眼睛,但一直没发现马广地有什么动作。
他坐进驾驶室里,心里像长了草,侧脸朝防护林那边一瞧,那一号已经拆散,白玉兰夹在姑娘们中间正往回来。
马广地和李晋并肩坐在扁担上,让背冲着大解放,打开手绢一看:“嘿!油饼!咸蛋!哟——还有纸条!”
李晋急忙从马广地手里接过纸条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歪歪扭扭的几行小字:
亲爱的白玉兰:
你好!
我实在太爱你了!
听说你带病参加夏锄,我特意让妈妈给你烙了两张油饼,煮了两个咸鸭蛋,请收下吧!
今晚九点,我在扎根碑那儿等你。
请切记!
此致
敬礼!
王明明
“他奶奶的,真是个不够揍的龟孙子玩意儿!”李晋一看,恨得登时咬牙切齿,双手把纸条撕得粉碎,骂了起来,“这家伙明明知道人家白玉兰有对象,还整这景!他爸爸口口声声不准知青恋爱,现在我明白了,纯粹是给他自己家定的政策,开的绿灯!”他停了停,更加气愤地说:“依我看,王明明搞的这花名堂,幕后准有王大愣当后台!”
马广地睁大了眼睛:“能吗?”
“差不多,”李晋好像很有把握,“根据这些迹象判断很有可能。王大愣调白玉兰到连队机关十有八九没安好肠子!”
“他娘的,鳖犊子!”马广地更是恨得咬牙切齿,“不能让他们得把!”
马广地在去空军农场的路口上挨了王明明那顿熊,一直怀恨在心。他想报复,一直找不到时机,再说也没有能力,也不敢,怕弄不好吃大亏。他一直忍气吞声,每见到王明明一次都恨得牙根疼。他曾经惋惜过好几次,说不定通过那两件衬衣就能和白玉兰联络上感情呢!直到去小兴安餐馆,他从李晋嘴里知道白玉兰和郑风华可以说是棒打不散的鸳鸯,才算死了心。现在,王明明这样神出鬼没地插手,使他心里又痒痒了:“倘若让他把白玉兰的感情联络走了,还不如让我联络来呢。”
他心里像打翻了的小醋罐子!
“喂——”马广地拿起一张油饼递给李晋,“吃了它,就算孝敬咱哥俩啦!”
“你别他妈下三烂!”李晋“啪”地一声把马广地递过来的油饼打出去老远,训斥他说,“你知道吗?君子不食嗟来之食!再说,这东西是搞肮脏勾当的,不怕埋汰了咱知识青年的嘴!”
王明明眼巴巴瞧着白玉兰和姑娘们分手走到自己铺的塑料布那儿坐下,休息了一会儿,像根本没发现塑料布上有什么似的,瞧瞧围着汽车买饭的人少了,她才走过来买了两个馒头和一碗菜。这个过程中的一举一动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他怀疑马广地偷走了他的手绢包,可是压根儿没发现马广地在那儿哈腰。再说,他也亲眼看见马广地在汽车这儿买了两份饭菜,回去后给了李晋一份。他心里嘀咕:真他妈的闹鬼了!
他纳闷得像得了霍乱症似的,索性从马广地和李晋身边走过,绕半个圈子探个究竟。
马广地发现王明明晃晃悠悠地走来,猜测来势不善,屁股靠李晋挪了挪,用胳膊肘碰他一下,李晋自然地抬起头来看了看王明明,知道了马广地碰他一下子的用意,一只手拿着馒头往嘴里送,一只手在暄垄沟里扒了个坑,拽一下马广地的衣襟,马广地心领神会,急忙伸手把刚才被李晋打掉的油饼捡过来,连同手绢包一起扔进坑里,又埋上了土。
王明明若无其事地溜达过来,眼睛在马广地和李晋身边撒眸着,什么也没有发现;又奔白玉兰那儿,走去一看,白玉兰侧卧在塑料布上,正迷迷糊糊地闭目养神休息,那手绢包无影无踪了。
王明明朝马广地瞪瞪眼珠子猜测:准是他搞了鬼!
马广地却像没事一样挑起桶吆喝起来:“喝水了,喝水了,谁喝水……”
开始铲地的哨声响了,仨俩成堆地躺着休息的人们开始回到自己的垄上继续铲起地来。
“哈哈哈……”李晋一手握着锄,一手拍拍正在身边吆喝的马广地的肩膀头,又褒又贬地开玩笑说,“我看你呀,干正经事儿差点劲儿,弄这路鬼头蛤蟆眼的事,还真挺干净利落!”
“嘿嘿嘿,”马广地一龇牙,“不敢当,不敢当!”
这时,有人招呼要喝水,马广地挑着桶,左一脚右一脚地横跨垄,朝招呼他的人走去。随着脚步跨垄,两个水桶里的水被荡得直溅水花。
王明明的歪门斜道,勾引得马广地想入非非,大白天做起了美梦:这几天,常发现郑风华心神不定的样子,有时还低头耷脑,像是心事重重,莫不是他和白玉兰有情况?要不,王明明这家伙怎么像白玉兰和郑风华根本没那回事那样,公然送吃投信约会?李晋分析的那一通听来头头是道,那是旧皇历,这人心隔肚皮,他又没钻到人家心里去看,也是没准星的事……要是白玉兰和郑风华铁了心,自己也只好认可,要是王明明想把白玉兰粘乎去,自己可就要动手了!
挂在天上的太阳像个大火球,炙烫的光芒腾腾地散射着,烤干了空气中的水分,使人喘气都觉得难受,渍渍汗水,从每个人的脸上往下流淌着。
整个夏锄大会战的战场上,找不到一个没有汗水的人。
战地广播站的大喇叭随着向前推动的人们不断移动,在一个劲儿地给大家鼓劲,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着肖副连长领着检查质量和速度的评比情况。
马广地挑着水,眼睛总是往连队机关的地段那儿撒眸,几次发现白玉兰拄着锄把弯腰咳嗽。
他是深有体会,这热感冒比冻着凉着感冒还难受。同宿舍里,有的知青感冒十天八天不见好,脑袋迷糊、发烧、干咳嗽,昨天晚上,他到小医院开了两瓶止咳糖浆全揣了来,根本也不按说明服,一要咳嗽就来一大口,很见效,没有大咳嗽起来。他瞧着白玉兰咳嗽得难受的样子,心里产生了怜悯。
哨声又响了,这是地里的第三顿饭。马广地见白玉兰刚铺下塑料布,又被姑娘们喊走了,推说自己感冒难受让李晋去买饭,在那瓶没开口的止咳糖浆商标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悄悄地送到了塑料布上。
“这个龟孙子!”王明明砰地推开车门,边骂边朝那儿走去。马广地鬼鬼祟祟的动作被他看得一清二楚。他大摇大摆、毫不怕人看着的样子走过去,故意瞧着马广地,拿起止咳糖浆晃一晃,启开瓶塞,对着嘴上咕噜咕噜喝两口,“嗖”地抛出老远,然后故意摇摇摆摆地朝大解放走去,进了驾驶室。
靠着大解放的三堵车厢板排了长长的三列长队,人们在有秩序的买饭。
马广地见李晋还没回来,瞧着王明明摇摆着走去的身影,恨得两眼直冒火星。他眉头一皱,急忙掏出那瓶喝了一多半的止咳糖浆,将剩下的咕噜咕噜倒在地上,往地上一跪,从裤前门襟里,放进裤兜里,尿了满满一小瓶尿,把瓶塞盖好,在商标上写上了个更大的马字,瞧着王明明脸转向自己这一面撒眸时,他故意站起来晃晃手里的止咳糖浆瓶,意思是:“你扔吧,老子还有!”接着,大步流星地朝白玉兰铺塑料布的地方走去,到了那儿,还特意举起来摇晃了两下,才放到塑料布上,然后又回到了自己和李晋休息放水桶的位置。
王明明坐在驾驶室里往外探着头,扇着芭蕉扇,瞧着马广地的一举一动,连热带气,就像拉着重车上大坡的老牛,闷哧闷哧直喘粗气。他伸长脖子瞧瞧那帮女知青搭的一号还没有拆散,“砰”的一声没好气地使劲推开车门,一个高儿跳下去,不管是垄沟垄台,踩着豆苗朝白玉兰铺放塑料布的地方走去,边走边骂骂唧唧:“他娘那个粪的!我放的油饼准是这个龟孙子弄走了,你能放,我也能拿,喝那一口很管用,嗓子眼很痛快,正好老子感冒,省得自己到医院去了!这回拿到手,还不扔了呢!”
他走到那儿,猛地一哈腰捡起止咳糖浆瓶,对着马广地做个鄙视的鬼脸,手举着止咳糖浆瓶像摇晃拨浪鼓似的洋洋得意地晃了几下,打开瓶塞,发狠的样子送到嘴就是一大口,等进了嗓子眼感觉出尿臊味时,已经咽进了肚里。
他把瓶口靠近鼻子闻了闻,从胃肠反上来的臊味和瓶子里浓烈的尿臊味汇合在一起,从他的嗓子眼,从鼻孔直往脑门上蹿,一阵恶心使他“啊——啊——”着哈下了腰,连“啊”几下子也没吐出来,只有两条涎水从口角上流了下来,看那样子,那滋味比吐出来还难受……
“哈哈哈……”马广地刚想拍着巴掌仰脸大笑,一下子又憋住了,自言自语地说,“他妈的,这才解恨呢!我早就说过,尿债要用尿来还。老子从空军部队农场买的那几件衬衣,能白让狗尿尿啦!”
王明明几次要吐都没吐出来,憋得眼角上夹着泪珠子,咳嗽着直起腰来,嘴里嘟噜噜骂着叫号似的指划了马广地几下,忽听身后传来嬉笑声,回头一看,是白玉兰等十多名女知青过来了。他狠狠瞪了马广地一眼,灰溜溜走了。
李晋端着一大碗菜,怀里捧着十来个馒头,只顾顺着垄沟往马广地这儿走了,没看见王明明那些鬼动作,到了马广地跟前,有头无尾地听他自言自语嘟囔,问:“你嘟嘟什么玩意儿,也不来接接,什么聊斋不聊斋的?”
“哈哈哈……”这回,马广地笑开怀地放开嗓子了,笑完,故意一字一板地说,“不是聊斋,而是尿债,我是说,尿债要用尿来还!”
“你这玩意儿新鲜,”李晋把菜碗递给马广地,戏谑地说,“什么他妈尿债不尿债的?”
马广地把菜碗接过来放在垄帮上没苗的地方,回手又接过四个馒头说:“老兄,这是自古以来没有的新鲜故事,你听着,我给你讲……”
他从兜里掏出小饭勺,边吃着边从头到尾地讲起来。
不知什么时候,丁悦纯戴着一顶树条编的遮阳帽凑到他俩身后,听了个明明白白。他几次忍不住想笑都硬憋回去了,马广地声音一落,他抹一把脸上的汗水,笑得前仰后合,半天才稳定下来说:“该!这是臊司令应得的报应,就该好好教训教训他!”
“喂喂,我说丁老弟,”马广地听“臊司令”这个词儿,央求地说,“你不早就许过愿,说要给我们讲讲这‘臊司令’的传奇故事吗?插这个空儿,就给来几段吧!”
“来几段?”丁悦纯自问自答地往前一凑,和他俩坐成个对面,“好,今天就来几段。”
丁悦纯有点儿讲演的小天才,在学校读书时就是同学中有名气的故事员,讲起故事来借助表情绘声绘色,描绘稻草如何如何好时,能讲成金条。他数学不好,文科好,尤其喜欢作文,他给全学年背诵着讲《革命家庭》那本书,不少人听了都掉了眼泪!
他轻轻咳嗽一声,亮一下嗓子,把听来的片断经过语言加工,声情并茂地讲起来:
“传奇传奇真稀奇,臊司令的故事能叫你笑破肚皮,听我慢慢地讲给你。”他故意像平常讲故事那样卖个关子,先来个小段,“话说咱知青没来农场时,群众就称王大愣的花花公子王明明是小兴安岭下欺男霸女的一只虎。就业农工家的姑娘有不少叫他骗奸、猥亵了没人敢说,干吃哑巴亏,就连贫下中农、中农的姑娘也没少让他调戏!这样的姑娘全连才十三个,长得没有上等的,数中等的有五六个。他没诚心和人家搞对象,却以搞对象名义让人牵线单独见过面,一面见说不上几句话就要抱住人家姑娘亲嘴,就像对待娼妇一样。听说这五六个中一见面就吓跑的有四个。有人恨得暗地里说他就像猪舍的种公猪一样。要是把全国专能调戏妇女的流氓和臭无赖都集中在一起选个官,他准够司令。
“连队里的姑娘他该琢磨的都琢磨了,该调戏的都调戏了,吓得有些姑娘一见他就老远躲着走,听说这家伙和那些司机唠起嗑来,常常埋怨满连队没个漂亮得像样的姑娘,到县城里去拉货卸粮,一看见漂亮的姑娘就迈不动步了……因此,有的叫他‘色迷’,有的叫他‘色棍’,叫来叫去,还是‘臊司令’这个外号叫住了。”
“好,这是臊司令外号的由来。”丁悦纯停一停继续说,“下面,咱讲传奇故事之一——”
“话说这天,好几个司机在车队值班室里聊天,王明明这小子一个人躺在炕上枕着值班行李眯眯着眼,睫毛一动一动的。有个司机平常总让他取笑和调理,一直想报复报复却没找到机会,这回,瞧着他那副德行一猜,估摸就是在闭着眼睛做梦想好事。这司机突然一抬头瞧着窗外大树底下说:‘哟,真没见过,这是哪来的大姑娘,两个大耳朵,梳着一条辫。’王明明这小子一听忽地坐起来,趴到窗台上问:‘在哪儿?在哪儿?’那司机用手指指离门前不远的大树底下说:‘你瞧,那不是嘛!两个大耳朵一条辫,就是长得丑点。’王明明瞪大眼珠子一看,原来是一头正在树底部蹭痒的老母猪……”
“哈哈哈……”李晋止不住哈哈大笑着,重复着,“两个大耳朵一条辫!”
“别笑别笑,”丁悦纯说,“还有更逗乐子的,下面请听传奇故事之二——
“咱们都知道,这地方交通不大方便,乘车比较困难,要想搭乘他的车,那老爷们小伙子的是干脆没门儿,最痛快的就是漂漂亮亮的大姑娘。
“话说有一次,王明明这家伙往县城粮库送粮,在土窑子村边大道上看见一个老太太领着一个姑娘招手请求搭乘。他放慢速度把车开到她们俩跟前刹住车,笑嘻嘻地推开车门把姑娘和老太太让进来。姑娘紧靠他坐着,他不时地斜眼瞧瞧,就被姑娘红扑扑的漂亮脸蛋儿吸引得神魂颠倒。他把车开到一个远离村庄的地方,故意把车弄出点儿动静刹住,装模作样地哈下腰瞧瞧车底下又回到车上,对老太太说:‘老大娘,车子出点小毛病,你用脚踩住这离合器,千万别动弹,让这位姑娘下来帮帮忙,给我递个钳子、扳子什么的,别着急,我一会儿就能修好,耽误不了你俩赶路。’老太太满口答应:‘中中中。’
“姑娘大方地随着他出了驾驶室。他拿着钳子钻进车底下敲敲这儿,敲敲那儿,指着输油管笑嘻嘻地对姑娘说:‘乡妹,来,你帮我用手把着这个管,机器出了点儿毛病。’朴实的乡妹搭车心切,虽说穿身新衣服跟着妈妈到土窑子串完亲戚要回家,也爬进去跪着,两手使劲捏着。王明明这家伙见娘俩都上了圈套,往外探探脑袋喊:‘老大娘呀,你使劲踩住啊一一你要是动一动,我们俩在底下就没命啦。’根本就没有汽车修理常识的老大娘一边答应着,一边使劲踩住离合器:‘师傅,你就放心吧!’
“王明明这家伙假装捅咕捅咕这儿,摸索摸索那儿,眼睛贼溜溜地直盯着姑娘漂亮的脸蛋,越瞧越觉得心里发痒,就一点点往姑娘跟前凑和,瞧准姑娘不注意,就用脸贴了姑娘的脸一下。姑娘不知他有邪心,以为他忙乎中无意碰撞到了自己。这家伙本想把姑娘搂抱住疯狂一阵,见姑娘这么漂亮,突然理智起来,心里打算干脆跟踪上去弄明白住哪姓啥名啥,日后能娶到家也算称心,要是抱住亲搂一阵,恐怕这打算就没希望了。他进一步打量,这姑娘比连队任何一个姑娘都漂亮……
“他的鬼主意拿定,胡乱摆弄了几下,说了声:‘乡妹,好了,多谢,让你受累了啦!’姑娘大大方方地笑笑,说了声‘没什么’,便爬了出去。他从另一侧也爬出去,噌地蹬上车门前踏板,进了驾驶室,姑娘也随即一猫腰上了车。
“这家伙有了鬼点子,显得格外殷勤了。汽车既快又不颠,当开到一个交叉路口时,娘俩提出要下车。这家伙热情地阻拦,问明白后拐进岔道一直开进了不远的一个村屯,按着老大娘的指点,车停到了村头的一个三间房门口。她俩热情地招呼他进屋歇歇再走。老大娘先进了障子大院,急忙拉开屋门,没等转身往屋里让这家伙,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从老大娘开门的胳膊下钻出去跑到院子里,高兴地喊着:‘妈妈回来了!妈妈回来了!’紧紧抱住那家伙以为是姑娘的年轻妈妈。年轻的妈妈把孩子抱起来,左脸蛋右脸蛋地亲昵起来。
“这家伙一看扭身就走,走出两步,扭回头气哼哼地吐了口唾沫,骂道:‘他妈的,原来是个臭老娘们儿……”
丁悦纯绘声绘色地讲到这里,逗得李晋和马广地笑得前仰后合。他正要继续往下讲,开始铲地的哨声响了。
“等等,”丁悦纯走后,马广地挑起水桶刚想换新水,李晋一把拽住他,严肃地说:“我再次告诉你,你一定要学会自爱,自爱的人别人才能尊重你。以后别再粘粘乎乎往人家白玉兰那儿凑和,她和郑风华青梅竹马,是棒打不散的鸳鸯,这个,老兄我心里最有底。你要自讨没趣弄出难堪来,别说到时候我不客气,刷你个大马勺!”
李晋义正辞严,瞪得马广地的脸红一块紫一块,憨笑又像傻笑两声,连连点头:“是是是,我一定听老兄的……”
“喂喂喂,”李晋往马广地跟前凑凑,缓和一下态度,说,“我想给你当红娘介绍个对象,不知你能不能看中?”
“哪儿的?”马广地顿时眉飞色舞,“你先说说,是怎么样个人!”
李晋郑重其事地说:“据我掌握一条信息,有个挺漂亮的山东姑娘来咱们连队走亲戚,其实呢,是来这里想找个对象扎下根。她家乡受了灾,父母早就故去。至于人品方面,我已做了初步调查,没有什么问题。论长相个头呢,也数中上流。你要是有意思的话,老兄我愿意给你卖卖力气,到时候弄杯喜酒喝。”
“喝喜酒倒好说,咱哥们啦。不过……”马广地犹豫了一下,“咱们堂堂城市人,找个山东大妹儿,太有点儿那个了……”
“好小子,你瞧不起山东人?山东那地方是咱老祖宗发源地之一,那里出的能人最多,光梁山就聚过一百单八将,现在中央许多大干部都是山东人……我的老祖宗也是山东人。你瞧不起山东人,人家山东人不知道能不能瞧起你呢!”李晋脑袋一歪像自己受了侮辱,冲马广地发出一阵连珠炮,“再说,你他妈臭美什么玩意儿,还大言不惭口口声声城市人,你叫下乡知识青年,下乡了,到乡下来了,是地地道道的农业户口了……”他说着一扬手表示出让马广地走开的样子:“瞧你这套浮皮潦草的臭世界观,真得接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去去,远点扇着吧!”
马广地叫李晋一顿抢白,服服帖帖地连连道歉:“好好好,我听你的。你说这山东大妹在哪儿吧?咱总得撒眸撤眸呀!”
“这是咱俩先私下说话,人家能不能看中你还两码事呢!告诉你啊——看不中,可不准埋汰人家!”李晋又教训了马广地一番,用手指指家属队地段那儿说,“在家属队临时工那一组里。你瞧,就是那个穿粉红色的确凉布衫,穿北京蓝裤子,梳着两条大辫的那个。”
嘿,也像白玉兰一样,穿粉红色的确凉布衫……马广地顺着李晋手指的地方,美滋滋自言自语地撒眸起来。
“来,我告诉你,”李晋让马广地把脸转向他说:“你假装无意地凑过去打眼看看,要是个头、长相大面上看中了,我再详细去给你了解。话说回来,咱也得摸摸人家,人家要是看不中咱,那也没招,你就算是猫咬鱼尿泡——空喜一场!”
“嘿,咱下乡知青不说,农业户口城市味!”马广地一拍胸脯说,“老兄,就凭咱这小伙儿这么帅,除了矮点儿没别的毛病,差不离的老丈母娘看了就准喜欢!”
李晋一扬手:“别油嘴滑舌地自吹自擂,去去去!”
马广地贪婪地往家属队地段那儿的粉红色的确凉衬衫瞧了一眼,挑着桶朝地头水缸大步流星地走去。
他舀上两半桶水挑上,急急忙忙在自己排分担的地段从左到右,给几个要水的喝完后,横跨着垄,越过机关、后勤等分担的地段后,边朝家属队那边走边喊,想一本正经,却弄出了一口油腔滑调味:“喝——水——啦——喝水啦!咱是十六排的送水员,今天高兴啦,学雷锋,做好事,给各位义务送水来了,快喝啦——快——喝——啦——再不喝要没了,这是淡淡的咸盐水,喝了又解渴又防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