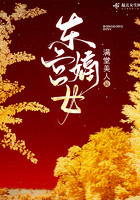腿有残疾的壮年人似乎此前并未学过武,打出的拳也毫无章法可言。面对刚冲上来的前几个家丁尚且能坚持,可随着家丁人数的逐渐增多,也渐渐呈现出体力不支的状态来。直到一个家丁的棍棒高高举起,趁他躲闪不及,直直落在他伤腿的膝盖上后,青年的身体也随着失去平衡而跪在了地上。“干!”他攥紧拳头,抬头怒目而视。元仪这个混蛋,说好的只是演一场戏呢?怎么这群人都一副凶神恶煞要杀了他的样子!元寿快速出拳想要回击刚刚袭击了他的那个家丁,忽然想到此前颜协反复嘱咐的,绝不能暴露武功,又半道将拳打歪了半分。结果他一击不中,却给了家丁机会,对方直接照他脸上来了一记拳,啐道,“敢打你爷爷?爷爷今日教你有去无回!狗崽子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居然敢来高府门前撒野……”家丁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又顺便给了已被打得无力还手的元寿飞起一脚。元寿只能护住要害将自己缩成一团,并开始后悔一开始为了耍帅而脱下的衣服。他错了,他真的不该脱衣服,而且他还应该穿厚点再来的。可是关键这和之前商量好的流程不一样啊。元仪可没和他说这群家丁是真打,而且来之前还反复保证救他的人一定会在他挨打的瞬间立刻出现。可是人呢?人在哪里?!元寿能感觉得到那些拳脚和棍棒正不断落在自己的背上和肩上,疼痛仿佛潜进了身体中,随着他血液的流动,蔓延到四肢百骸。只是疼得多了也有些麻木,他的眼皮渐渐开始不断合拢,随着合眼的时间越来越长,人也愈发昏昏沉沉起来。人群里传来百姓的骚动,元寿感觉到背上的痛感忽然轻减了不少。目光越过层层家丁阻隔,他看到了一个少年。一个肤色黝黑,眼神像狼一般的少年。少年手持一柄剑,却未出鞘,只当作木棍用来赶走那些围打他的高府家丁。所以,这就是……郡主要找的那个少年?这疑惑很快得到了解答。因为元寿听见了太子的声音,也听见了元仪的声音,在说,“全都围起来,这里的人一个也不准放过。”百姓们七嘴八舌,为太子喝彩叫好。是元仪来了……元寿再一次热泪盈眶。昏过去前想:等老子醒了,一定跟你没完!…………那少年的皮肤粗糙黝黑,瞳孔在日光下呈现琥珀色,长长的睫毛在他眼底投下一小片阴影,遮住几分野性的凶光。少年身上被捆了绳子,又被颜协的人压着肩膀跪下,却也不挣扎,只沉默的盯着李容与,像极了一只无法被驯服的山狼。“你叫什么名字?”李容与给手下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们让他站起来回话。少年起身,却没有去坐那些人搬来的椅子,以一种极其防备的姿态紧盯李容与,反问道,“你叫什么名字?”旁边侍卫顿时怒喝,“大胆!郡主名讳,岂是容你随便问的?”李容与摆摆手,示意他们不要再说话,温和对少年道,“我叫李容与。”少年想了想,“秦榔儿。”李容与笑了,“好,秦榔儿。”又问,“你为何救高府门前那个青年人?”秦榔儿警惕看着她,“你为何将我捆来此处?”李容与道,“我只是将你请来此处,捆你是为了防止你离开,不得已而为之,望你能够见谅。”秦榔儿道,“我救那人只是因为不想看他无辜惨死,并没什么别的原因。”李容与似乎有些明白了秦榔儿的意思,应该是在与自己对等交换信息。若自己想得到他的回答,就一定要先回答他的问题才行。李容与想了想,决定干脆收回先前想问的其他问题,直接表明态度,“秦榔儿,我无意伤害你,不过目前因为一些缘由,也不能放你走,所以还要委屈你些时日,暂时住在这里。”秦榔儿眉头微皱,他能听得出来眼前这个少女并不是在与他商量,而是在向他宣布结果,可他依旧想试着争取一下。“给我三天时间。”李容与摇摇头,“半天都不行。”秦榔儿有些沮丧,又有些愤怒,“我答应了别人!”李容与哦了一声,饶有兴致,“你答应了谁?”秦榔儿抿唇不语。李容与也不催,径自吩咐道,“颜叔,给他挑一方僻静些的院子,再派几个仆从左右照看着,莫怠慢了。”秦榔儿拳头紧紧攥起,眼睛一刻不离她。眼看着自己就要被带下去,终于忍不住开口讨价还价,“若我告诉了你,你可以放我离开?”李容与走到他身前,像对待一只小野兽那样拍了拍他肩膀,笑眯眯道,“不可以,不过若你告诉我,我倒是可以考虑常去看看你,为你带些外面的消息。”被拍了肩膀,秦榔儿脸上顿时飘起一片绯红,原本坚定的眼神也变得有些闪躲,最后还是没有说出什么,任由那些人将他带离了李容与所在的地方。宝珠看着秦榔儿离开的背影,忍不住感慨,“原来这就是江湖游侠啊。”先前总听太子殿下称呼自己是江湖游侠,她还纳闷了好久,不知这江湖游侠到底是什么,竟能吸引得太子连皇位都不要继承了。原来便是这样的人么?李容与问,“你觉得他这种人如何?”宝珠犹犹豫豫,“奴婢说不上来,似乎…是个很重信义的人呢。”李容与点头,“是啊,这样的人,对于承诺往往看得比命更重要,不过也很容易落入圈套,为人所利用。”宝珠笑道,“所以郡主您关他其实是在救他对么?”李容与摇头,“救他也不全为了救他。”又问,“父王在做什么?”宝珠道,“据说带元寿去大牢找那些家丁去了,要为他出气呢。”李容与道,“叫他们现在不要将人打死,以免落人口舌。待过几天大理寺审完高阳的案子,这些伥鬼自随他们收拾。”……刑部大牢中。李庸已将监守狱卒遣散,只留了元寿元仪和几个近卫。元寿腿上腰上皆裹了一层又一层的布,由几人合力抬着,看上去有些滑稽。只见他从怀中抽出几根细长的银针来,冷笑着向已经被按住那几个家丁身体上扎去,带着刻骨的恨意,“敢打你爷爷?嗯?娘的,说!到底谁才是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