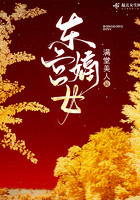谢玄?听见这个名字,李容与眼中笑意顿消,干脆利落道,“不见。”颜协面露犹豫,“可是他说,此事…和芸娘有关。”…………长安城的少年们之中,若论起美,那李容与的兄长、别号公子瑾的郡王李容牧自然是当之无愧的第一美人。可若论起俊,却还得是谢家嫡长孙谢玄更胜一筹。谢玄天生眼窝深邃,剑眉星目,鼻梁直而挺,唇薄而色淡。就像一副山水画,画面整洁干净,颜色清淡俊雅,没有一笔是浓墨重彩,却教人忍不住看了又看。这便是谢玄。只是再俊朗的少年,经过七年冷漠的朝夕相对后,也足够让人对他的容貌熟视无睹了。李容与也早就看惯了他喊过自己名字后发出的长久沉默。只是这一次又略有不同。因为此时的谢玄还很年轻,也还没有四年后那样的老成持重。他眼神干净而柔和,语气带着轻快,“容与。”谢玄的祖父是太子之师,所以她与谢玄自小相熟。是以谢玄在面对她时,时常没有身为属下的自觉,依旧还按着儿时的叫法,直接唤她名字。可她却不愿意了。李容与皱起眉,语气疏离而淡漠,“谢郎将找我有什么事?”距离瞬间被拉远。谢玄几分茫然不解。不过他早已学会了不动声色的将情绪隐藏。见李容与对自己疏远,也随之调整了态度,垂头恭敬道,“是大义公主遣臣来请…您,有时间过府一叙。”芸娘?李容与一阵头疼,不知她又闹什么幺蛾子,却还是点头应下,“知道了,替我传话给大义公主,说我得了空就过去。”谢玄抬眼看她,本欲再说些什么,可撞上了那一双冷漠的眼睛以后,顿时没了再说下去的想法,很快顺应着李容与的心意,行礼退下了。他并不知道她为什么忽然对自己转变了态度。但是他知道,现下,或者说在找出原因将误解解开之前,他都应该保持回避的状态,不然只会让两人的关系从此愈发恶化下去。谢玄离开,颜协便也很快跟着退下做事去了。宝珠积攒了半天的不满才终于得以发泄,“道貌岸然!”自从上回郡主和她表明不想嫁给谢玄的想法以后,她现在看谢玄做什么都觉得是别有企图。李容与并没有反驳她的说法,或者说,她根本没有注意到宝珠此刻的愤怒,她一心都用在了思考谢玄的事情上。看今天这样,想来芸娘不但没有成功勾引到谢玄,败坏他声名,还反过来被他利用成进东宫的借口了啊。不过谢玄也确实该找她了。毕竟前世这时候她对谢玄信任无比,常将他当作知己,隔天便去一趟谢府,找他倾吐自己对父王的各种不满。想必自己这边突然没了音信,谢玄也在奇怪吧。不过谢玄是个聪明人。而聪明的人大都骄傲。这一次在自己这里吃了瘪,此后应该就不会再往自己跟前凑了。只不过还有一件事……李容与突然站起身来。一旁犹在心中不平的宝珠顿时打起精神,目光灼灼望着她。“我们走。”宝珠忙跟上,“郡主,咱们去哪里?”“高府。”她现在改主意了,她要亲自去引可能出现的秦榔儿,然后杀了高阳,快点将这件事解决,让芸娘对自己死心塌地。不然夜长梦多,若是最后芸娘被谢玄驯服,临阵倒戈,那她可就亏大了。…………熙熙攘攘的大街上,车马的喧嚣声与人群的吵嚷声不绝于耳,热闹非常。而在这样嘈杂的闹市尽头,却坐落着一座森严府邸,仿佛被一道无形的屏障罩起,将平头百姓们的一切声音和情绪隔绝在外。没有哪一个百姓或小贩敢走近它十丈之内。甚至没有哪一个人敢抬头望一眼那紧闭的铁门或高耸的围墙。百姓们就像看不见那座府邸一样照常进行着一天的生活与工作。只有不时驶进去的官家马车,提醒着这座府邸的真实性,并非是繁华市集中的海市蜃楼。那便是监察御史高阳的府宅。监察御史这个官职,品阶虽然不高,但是职权很大。再加上高阳出身于高门大族,平日里出手极为阔绰,且常在府中宴请宾客,所以在朝廷大臣间颇有一副好人缘。但是在百姓间就并非如此了。他因为讨厌尘世烟火气,慕羡“往来无白丁”的清净,便下令高府十丈以内不准任何百姓靠近,违令者便会遭到高府家丁的毒打,轻者卧床一月,重者甚至会落下终身残疾。久而久之,百姓们便都长了记性,绝不越过那道无形的线,甚至到最后连提起那个颁布了规则的府邸也不敢了。时间正值晌午,纵使再热闹的市集此刻也是偃旗息鼓,老实窝在静谧的春光里休养生息。可却偏有些心急的人,非要企图更早打破这份安逸。街道两旁略作休憩的商贩们只见一个穿着打满补丁的裤子、裸露着精壮上半身的,约莫二三十岁左右的壮年人,不知从哪里窜出来,正拖着腿一瘸一拐向高府门前走去。他一边走一边大声陈述,讲自己月前是如何不小心踩进了“线”里,又是如何被高府家丁活捉,并被残忍的打断了一条腿的。青年人边喊边向高府走,眼看着就要再度越界,高府门前的侍卫也开始蓄势待发。有看不过眼的长安城大娘忙走上去拉他,欲将他往回拽,“小伙子,别走了。再走下去就不是废一条腿,而是要赔上性命了。”那人却将胳膊从大娘手中抽回,看着身后渐渐聚拢起的人群,几近热泪盈眶道,“高阳为官二十余载,做尽了欺压百姓,残害忠良之事,如今我已成废人,也不怕他们再废我一次。今日,就算是舍了这条命,我也要为民众伸张正义!”百姓们纷纷摇头叹息,留停在原地,悲观的张望。却无人敢再上前。在人们目光的注视下,青年终于拖着残腿,一脚迈进了那道无形的线内。而高府门前的家丁们也随即手持各类棍棒或农具,气势汹汹向他走了过来。